原标题:癌症从何而来,又为何难以治愈?
原文作者丨[美]雅典娜·阿克蒂皮斯
摘编丨安也

《狡猾的细胞:癌症的进化故事与治愈之道》,[美]雅典娜·阿克蒂皮斯 著,李兆栋 译,中信出版(35.870, 0.75, 2.14%)集团2021年6月版。
大约20亿年前,多细胞生物出现,生命随即也开始了与癌症的苦苦纠缠。我们想到地球生命的时候,通常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动物和植物这样的多细胞生物,其组成包含不止一个细胞。从根本上来讲,多细胞生物的细胞通过它们之间的分工、合作和协调,来完成其生存所需的所有功能。而另一方面,单细胞生命形式(如细菌、酵母和原生生物)则只由一个细胞组成,该细胞独立完成使其自身存活的所有工作。
在多细胞生物在演化长河中赢得一席之地之前的数十亿年里,我们这个星球一直都由单细胞生物主宰着。在单细胞生物占据统治地位的20亿年里,世界上是没有癌症的,然而随着多细胞生物的到来,我们的世界也迎来了一位新成员:癌症。
癌症是我们的一部分,从我们以多细胞生物的形式存在伊始,癌症就成了我们身体里的一部分。从埃及木乃伊到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狩猎采集者,我们在这些古人类的骨骼中都发现了癌症的遗迹。科学家在170万年前活动于“人类摇篮”南非的人类祖先的骨头中发现了癌,而癌症的化石证据则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前的哺乳动物、鱼类和鸟类的骨骼当中就有癌存在了。早在恐龙统治我们这个星球的时候,甚至更早,在生命还以微观形式存在的时候,癌症就已经出现了。癌症,始于我们所知的大部分生物存在之前。
要想有效控制癌症,我们必须了解其背后在演化上和生态上的动力。而且,我们还必须改变我们思考癌症的方式,不再把癌症当成一个我们需要暂时面对且能够从容应对的挑战,而是将其视为我们人类作为多细胞生物而拥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多细胞生命从演化中产生之前,癌症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时并没有能够容纳癌细胞增殖并最终侵入的生命有机体,然而多细胞生命一旦出现,癌症就应运而生。而作为多种细胞之间相互合作的多细胞生物的典范,我们人类终将无法摆脱与癌症不可分割的命运。

电影《抗癌的我》(2011)剧照。
与癌症苦苦争斗的并非只有人类
在这里,我们将看到多种细胞如何构成了我们的身体,它们以多种不同形式协作,使我们的身体正常运转——例如,控制细胞增殖,将资源分配给有需要的细胞,以及构建复杂的器官和组织结构。我们还将看到癌细胞是如何演化出利用我们身体里的细胞协作特性的能力的:不受控制地增殖,掠夺我们体内的资源,甚至将我们的身体组织变成专供癌细胞自身生存的理想之所。简而言之,癌细胞在这场构成多细胞生命基础的最基本的游戏当中,极尽欺骗之能事。
更好地了解癌症的本质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地预防和治疗癌症,也让我们看到,与癌症苦苦争斗的并非只有我们人类,其他各式各样的多细胞生物都受到癌症的影响。我们与癌症在演化上的关系造就了今天的我们。而且,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理解什么是癌症,我们就必须要弄明白它是如何演化的,以及我们是如何与之一起演化的。
要认清什么是癌症,以及它是如何演化的,我们可以将目光转向自然界。凤头仙人掌就是一个最美的例子。由于损伤或感染,仙人掌顶端的细胞有时会发生变异。这些变异会破坏植物生长过程中控制细胞增殖的正常程序,从而经常导致仙人掌形成某些异乎寻常的构造:看起来像头戴王冠的沙漠仙人掌,外观像大脑的盆栽仙人掌,以及具有多角形几何结构、让人联想到现代艺术的花园仙人掌。凤头仙人掌因其美丽而独特的变异构造,受到专业植物学家以及爱在自家后院摆弄仙人掌的爱好者们的追捧。
由于正常的生长模式遭到破坏,仙人掌会长得奇形怪状,从而造就了许多美丽而独特的生长模式,与动物的癌症相似。植物身上这些类似于癌症的现象被称为缀化,可能对其适应环境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开花变少,或者更易受伤、患病。不过,如果照料得当,这些植物也能够带着这些类似癌症的形式存活数十年。

图片从左至右、从上到下依次为:凤头仙人掌(Carnegiea gigantea);“大脑仙人掌”(Mammillaria elongata cristata);“图腾柱仙人掌”(Pachycereus schottii f. monstrosus)和牙买加天轮柱(Cereus jamacaru f. cristatus)。
很多年前,我在亚利桑那州第一次看到凤头仙人掌时,就被它美丽的几何构造吸引住了。回到酒店之后,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观赏这些自然生物构造的照片,并阅读了它们的相关资料。我了解到,变异凤头仙人掌的生长模式被打乱的原因,有时是暴风雨造成的破坏,有时是细菌或病毒感染,有时是其生长过程中发生的遗传突变。
我还了解到,破坏植物生长方式的变异并非仙人掌所独有——从蒲公英到松树,它们在许多植物身上都会发生。有一个术语专门用来描述植物中这些被打乱的生长模式,叫缀化(fasciation)。缀化植物通常比它们非缀化的近亲更娇弱,它们有时不能正常开花,因此也就更难再生与繁殖——但是,园丁和植物学家常会悉心照料缀化植物,帮助其繁殖。而在精心照料下,凤头仙人掌及其他缀化植物能够带着这些类似癌的形态结构存活达数十年之久。
为什么癌症在所有形式的多细胞生物中会如此普遍?
了解凤头仙人掌,让我开始着迷于探索来自不同生命形式的癌症。当时我心想:如果我们要理解癌症——了解什么是癌症,以及它为什么会威胁到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那我们就需要知道癌症从何而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穿过演化之树,去探寻癌症在生命演化上的起源。在继续了解癌症演化起源的过程中,我发现癌症和类癌症的结构在多细胞生物中随处可见。不单单是仙人掌,无数其他生物都会生长出这种类似癌症的结构。我找到了长着类似癌组织的蘑菇、珊瑚、藻类以及昆虫的照片,并发现癌症在各种动物中也很常见,不论是野生动物、动物园里的动物,还是与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家养动物。
我想弄清楚,为什么癌症在所有形式的多细胞生物中会如此普遍?癌症之所以成为多细胞生命独有的问题,正是因为多细胞生命由许多细胞组成,这些细胞通常要相互配合,调整各自的行为,使我们成为具有功能的生物。单细胞生命形式不会患上癌症,因为它们仅仅由一个细胞组成,也就是说,对单细胞生物而言,细胞的增殖就是其生命的繁殖,二者毫无二致。但对于多细胞生命而言,过多的细胞增殖会破坏整个生命体的正常生长和组织结构。
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由数万亿个细胞组成,这些细胞无时无刻不在互相交流并协调彼此的行为,从而使我们体内的各项功能正常运转。我们体内的细胞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是地球上人口总量的4000多倍。我们每个人就是30万亿个正在互相合作、演化、消耗能量、计算、表达基因并生产蛋白质的细胞,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世界。这些细胞中的每一个都像是我们体内的一个小矮人,从环境中获取信息,并通过复杂的遗传基因网络处理这些信息,再根据这些输入的信息改变行为,做出反应。
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一套基因组、自己对基因的独特表达(即该细胞正在制造的特定蛋白质),以及自己独特的生理状态和行为。细胞在我们身体内部的合作令人叹为观止。这30万亿个细胞是如何让我们看起来像拥有一系列特定目标的单一实体生物的?是什么让这么多的细胞如此协调统一?
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可以从演化生物学中找到:之所以我们在行为和感觉上像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因为演化把我们每个人塑造成了一个不同细胞相互合作的社会。或许,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像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存在,是因为演化让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如此行事。近10亿年的演化历程塑造了多细胞生物体,让每个细胞的行为方式有利于细胞合作社会,即多细胞生物体的生存和繁殖。
我们体内的细胞会限制自身的增殖、实行任务分工、协调资源利用,甚至会为了整个生物体的利益而选择自杀。我们体内的协调合作的规模,是人类迄今为止从未达到的:我们体内的细胞成功造就了一个乌托邦,它们为了整个身体的利益,共享资源、维护共同生存的环境、调控着每一个细胞的行为。

电影《抗癌的我》(2011)剧照。
然而,细胞之间的协作有时候也会破裂。协作的破裂会引发体内的一系列演化和生态程序,最终产生细胞之间相互欺骗的终极形态:癌症。当有些细胞停止为了多细胞生物体的利益而协作,开始过度使用资源、破坏体内的公共环境,并失控地增殖扩张的时候,癌症就出现了。尽管这些狡诈的细胞会殃及它们所在的身体的健康和生存,但与体内的正常细胞相比,它们却具有演化上的优势。
需要同时具有两种视角才能了解什么是癌症
尽管我们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个不可分割的个体,但从根本上讲我们并非如此。演化把我们塑造成多细胞生物,令我们具有不可思议的功能,但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由一大群细胞组成的事实。也正因为我们由一大群细胞组成,演化过程会在我们体内自然发生,细胞能够像自然界中的生物一样演化。这对思考我们自身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视角。在传统观念中,我们是单一的整体,是相对静态的“自我”。但其实,不仅我们的身体由数万亿单个细胞组成,而且这数万亿细胞组成的群落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我们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而是由许多实体组成。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组成我们的细胞群体不断变化,通常朝着让我们更容易得癌症的方向发展。
当然,细胞是我们身体组成的一部分,但它们也可自成独立的王国。细胞可以表达基因,可以处理信息,也能做出各种举动——迁移、消耗资源,并建立细胞外结构,如组织结构。此外,它们也在我们体内复杂的生态环境中不断演化。细胞是我们的一部分,细胞同时也是在我们身体内部不断演化的特殊实体——我们需要同时具有这两种视角才能了解什么是癌症,以及我们为什么容易患上癌症。

电影《生存证明》(2008)海报。讲述了著名医生丹尼斯史莱门研制一种治疗乳腺癌的新药“贺癌平”(Herceptin)的感人过程。
从我们身体的角度来看,癌症是对我们生存和健康的威胁,而从细胞的角度来看,癌细胞只是在做这个星球上所有其他生物都在做的事情:在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当中不断演化,哪怕有时其演化方式会给其所属的系统带来灭顶之灾。这就造成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演化局面:演化过程青睐能更好地抑制癌症发生的身体,但演化同时也让体内具有癌细胞特征(例如快速增殖和高新陈代谢率)的细胞更有优势。两者如何并存?一方面,演化有利于癌细胞,另一方面演化又需要抑制癌症。
我们体内细胞之间合作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然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面对体内细胞的作弊与叛变,我们的身体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面临癌症的威胁,我们仍然能生存下来,并繁衍不息。数十亿年来,多细胞生物体已演化出多种不同的癌症抑制机制。这些癌症抑制系统使我们得以将叛变的细胞圈在可控范围之内。通过考察不同的物种,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癌症抑制系统的种类之丰富、威力之强大,并从中得到启发,从而找到更有效的治疗癌症的方法。凤头仙人掌可以与体内的“癌组织”共同生存长达数十年之久,或许我们人类也可以做到。
在我了解癌症演化上的本质之前,我觉得癌症不过是一种没有多大意思的疾病。我的研究工作集中在与生命演化有关的深层而根本的问题上:为什么这么多生物都具有社会性?在群体里所谓的作弊者随时可能大量出现的情况下,是什么促成了个体之间持久而稳定的合作关系?我的研究兴趣侧重于理论问题,因此我总是回避那种看起来有大量事实需要记忆,又缺乏一个理论框架将这些事实整合在一起的研究主题。癌症似乎就是一个这样的研究主题——没有理论基础,只有大量关于这个机制那个机制的研究,当中却没有蕴含什么基本原理等待我去发现。癌症对人类健康影响重大,因此当然值得研究,只是我个人对研究它没有兴趣。
两种不同尺度上的演化的角逐,正是癌症存在的缘由
后来,我到了亚利桑那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开始与约翰·佩珀(JohnPepper)合作,他是肿瘤演化研究的先驱之一,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我意识到,癌症其实就是我已经在研究的主题在细胞层面上的实例:在作弊者存在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演化系统如何克服困难,维持个体间的合作关系。
我对癌症的看法开始改变,意识到癌症也是在我们体内的生态系统中不断演化的一种“生物”,它同样遵循着其他所有演化和生态系统都遵循的法则。将癌症放到演化生物学的框架中为我们理解其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20世纪演化思想先驱之一、伟大的演化生物学家特奥多修斯·多布任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曾经说过:“不从演化角度来理解,生物学就没有任何意义。”我意识到,此前,癌症生物学对我来说毫无章法,是因为我没有从演化和生态学的角度来思考癌症。
如果多布任斯基今天还健在的话,他可能会说:“不从演化角度来理解,癌症生物学就没有任何意义。”演化、生态学和合作理论为我们理解癌症为何如此复杂、强大而充满破坏力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它们同样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癌症如何塑造了——并继续塑造着——所有的多细胞生物。
演化论从两个层面解释了癌症。首先,它告诉我们人体细胞当中发生的演化(通常被称为体细胞演化)如何导致了癌症的发生。癌症将演化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体内的细胞正处在不断的演化中,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各不相同,有些细胞增殖速度更快,存活时间更长,因此这些细胞会在下一代中占比更多,最终主导整个细胞群落。这是自然选择下的演化,同样的过程也推动着自然界中的生物演化。
此外,演化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癌症在地球上的生命历程当中会一直存在。生物已经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演化来阻止癌症的发生,也就是让体细胞的演化保持受控状态,我们也因此能够拥有足够长的寿命,取得演化上的成功。这些癌症抑制系统让多细胞生命的出现成为可能——如果没有它们,多细胞生物永远也无法克服内部细胞作弊和叛变所带来的挑战。然而,这些癌症抑制系统并非十全十美,从演化上来讲,把将来有可能癌变的细胞百分百地控制住是不可能的。

电影《抗癌的我》(2011)剧照。
我们之所以不能完全抑制癌症发生,有多个原因,每个原因都有其独特之处。例如,其中一个原因是生物要在抑制癌症与其他影响生物适应性的特性(例如生育能力)之间权衡利弊。有些情况下,生物的低患癌风险与低生育能力之间存在相关性,从而给抑制癌症的生物造成了一种演化上的困境。
此外,我们过去和现在所处的生存环境不尽相同:诸如香烟之类会诱导基因变异的物质,以及体力活动减少等生活方式的改变,让我们更易身患癌症。另外还有一个更加奇特的原因:在我们生长的过程中,我们遗传自父亲的基因与母亲的基因之间发生着一场战争,遗传自父亲的某些基因,其功能在表观遗传上被设定为促进细胞生长和增殖,从而增加了我们患癌的风险。细胞通过体细胞演化在体内不断变化,而身体却无法演化出完全抑制体细胞演化的能力,两种不同尺度上的演化的角逐,正是癌症存在的缘由。
只要有多细胞生物的存在,癌症就不会消失
体内的环境会对可能癌变的细胞产生极大的影响,决定其是死亡还是生存下来并繁衍肆虐。在癌症生物学这门学科中,肿瘤所处的环境被称作肿瘤微环境,本质上就是肿瘤所处的生态系统,它与自然界中的生态系统有很多相似性。肿瘤的生态系统能够提供必需的资源,使得肿瘤细胞得以生存并不断繁衍;不过,当资源耗尽,代谢废物积聚过多,免疫系统开始“猎杀”癌细胞时,这个生态系统也会给癌细胞的生存造成威胁。
癌细胞会改变其周围的环境。例如,它们会不断消耗葡萄糖等资源,使得相邻细胞的资源供应减少,把诸如酸之类的代谢废物留在环境中。但是,这些变化会破坏癌细胞所处的生态环境,使癌细胞在其中难以存活。对微环境的破坏也会给癌细胞造成选择压力,迫使它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能转移到体内更适合生存的其他环境的癌细胞将会留下更多的后代细胞,从而推动了癌细胞向侵袭性和易转移的方向演化。要理解癌症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生态学角度的思考至关重要。正如我们不了解生物周围的生存环境就无法了解它们如何以及为何演化一样,如果不了解恶性肿瘤内部以及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变化的话,我们也无法理解癌症的演化方式和原因。
人们常常把癌症比喻成一场战争——病人在其中“战斗”“拼杀”,最终“胜利”或“失败”。战争的隐喻铿锵有力,极富感染力,有利于我们调动一切力量来支持癌症研究,用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人们紧紧地团结起来。但这样的比喻也可能会误导人,因为癌症本质上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无法将其彻底清除。如果我们将癌症视为要根除的敌人,那么对癌症采取激进的治疗方法似乎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们不看清癌症的本质——癌细胞各不相同,而且会随着我们采取的各种癌症治疗手段不断演化,我们就可能会对比较温和的治疗手段所产生的效果认识不足,甚或完全否定。

电影《星运里的错》(2014)剧照。
战争的隐喻鼓励我们用激进的眼光来看待癌症,还可能会导致其他后果。我们用大剂量药物治疗癌症时,会给具有抗药性的细胞带来演化上的优势,从而降低长期治疗和控制的效果。对于癌症晚期的患者,采用最高剂量的疗法通常并非理想策略。用激进的态度对待癌症也可能对癌症预防产生负面影响。当人们看到关于癌症的战争隐喻时,会更少去采取某些能够预防癌症的措施,比如戒烟。此外,与治疗有关的激进的词语也会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更多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癌症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说的敌人。癌症并非一支行动有序、整齐划一的军队,团结一致,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相反,它只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各不相同的细胞,面对治疗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与癌症的战斗,是与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演化——的战斗。我们可以使这个过程放慢脚步,或者改变其行进的方向,但我们不能让它停止。
癌症是演化的实体象征,是我们体内的演化。我们之所以会患上癌症,正是因为我们是由一群在我们一生当中不断演化的细胞组成。我们这个星球上只要有多细胞生物的存在,癌症就不会消失。我们越早认识并接受这一点,就能越早利用我们的知识来有效地控制它。
我们无法赢得与演化过程的战争,我们无法赢得与我们体内生态变化过程的战争,我们也无法赢得与在多细胞合作的过程中搭顺风车的细胞的战争。不过,我们可以改变这个过程,降低它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采取某些措施,把癌症变得更加良性、温和——换句话说,把癌症变成可以与我们和平相处的东西。
一种是唯有斩草除根,否则誓不罢休,另一种则是尝试利用癌症的弱点将它控制住——抗癌战争的两种策略,就像雅典娜和阿瑞斯这两位希腊战神各自的战争策略一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在一个希腊家庭中长大,一开始住在雅典,后来搬到了芝加哥的郊区,希腊神话是我童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由祖母雅典娜(我的名字就是随她)抚养的,我自然对了解与自己同名的女神很感兴趣。雅典娜是一位女神,她代表着智慧与战争;但她并不掌管一切战争,她是战略决策的女神。雅典娜的获胜并非通过粗暴的武力,而是准确认识战争目标,对敌人的弱点了如指掌,最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以免伤及无辜。而战神阿瑞斯在战争当中则总是以最大的侵略性,不惜一切代价,给敌人造成最大的伤害。
以上两种方式哪种更适合对付癌症?我们应该像战神阿瑞斯一样诉诸蛮力,还是应该像雅典娜一样制定一个充分利用敌人弱点的战略?根据我们目前对癌症的了解,很明显是雅典娜的策略更有可能延长癌症患者的寿命,同时也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的名字随她。)
作为多细胞生命体,我们一生中不可避免地要与癌症相伴。癌症不仅仅是一种疾病,它更是一扇窗口,能够帮助我们探索生命的起源、认识大规模合作所面临的难题、理解多细胞生物的本质以及演化过程本身的奥秘。
作者丨[美]雅典娜·阿克蒂皮斯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张进
导语校对丨陈荻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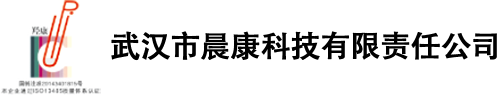
 APP--双知双行:
APP--双知双行: